1989年,胡錫進是一名爭取民主的抗議學生。如果6月4日前沒有離開天安門廣場,他可能永遠不會掌管中國一家頗具影響力的党媒。
現年56歲的胡錫進11年前開始擔任《環球時報》總編輯,是一位爭議性人物。在他領導下,《環球時報》因其強烈的民族主義言論而廣為人知,在國內外毀譽參半。報紙的社評一般由胡錫進構思,下屬主筆,常被外媒引述,用於解讀中國政府決策。
六四之後,胡錫進在90年代成了一名駐南斯拉夫的戰地記者。現在他堅信中國必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。不過,他仍批判地看待政府管治。譬如,他主張擴大言論自由,減少審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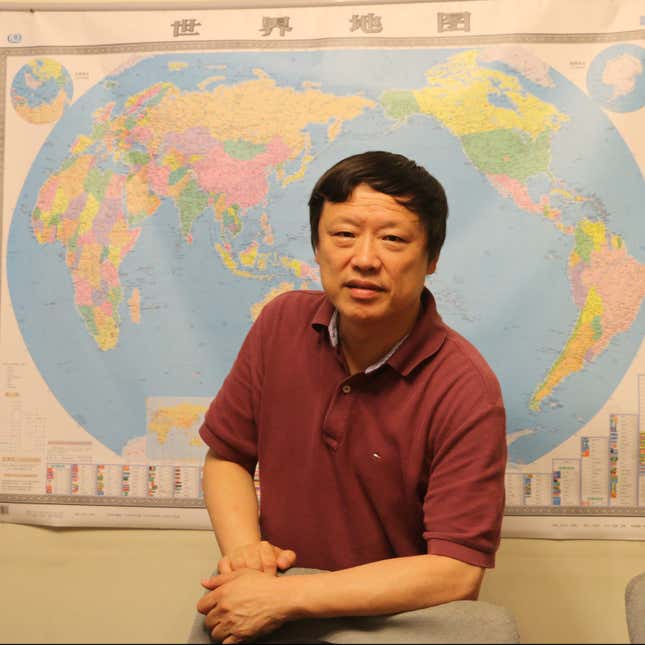
近日,胡錫進在《環球時報》北京辦公室接受了石英的專訪。他談到了自己鮮為人知的過去,中美之間「愛恨交織」的關係,以及他帶領的這家黨媒在中共政治宣傳中扮演的角色。以下是採訪實錄,略有編輯。
「我們是市場化媒體」
首先,稱呼《環球時報》為黨媒、官媒是否準確?
我覺得不是。黨媒、官媒這個詞不準確。它沒法描述中國媒體的現狀。《南方周末》也是黨媒,我們倆報紙一樣嗎?我們的體系完全一樣,我們都是「黨媒」、都是「官媒」。但是我們的價值觀有所不同。
《人民日報》、新華社這是黨媒、官媒。我們的報紙不能從這個角度來認識。我們就是市場化的媒體。在中國的市場化媒體,都會有一個管理部門,但是我們有一定的靈活度。我們是市場化媒體,這個詞對於中國來說更加準確。我們靠市場生存,不是靠國家財政,不是靠別的。《環球時報》是獨立核算的企業,自負盈虧,收入主要是發行及廣告。
所以你有兩個老闆,一個是政府,一個是市場,兩個老闆誰更重要?
就今天,具體的某一天來說,是政府重要。因為它要是反對我們,它就有手段能夠制裁我們。從長遠看,兩個同等重要。因為沒有老百姓,沒有大家支持,我沒有影響力了,政府也不會理我。沒有老百姓,我報紙就死掉了。
《環球時報》被外媒廣泛關注,是因為你們的社評嗎?
高端讀者比較關注社評,外媒也關注社評。但普通讀者還有讀故事的,頭版上面大的故事也有很多人讀。但是環球時報的影響力主要是來自於評論,尤其是社評。
有《環球時報》的前僱員說你覺得只要被外媒引用了就是好事,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報道?
總的來說受關注是好事。但我們不是為了外媒活着。首先對我們最重要的是能生存。要生存,就要在國內有影響力。國內對我們報紙的認可度,以及我們聲音在國內的傳播,這是我最重視的。

許多外媒認為你們的社評、評論可以當作中共官方聲音來解讀,這是一個誤區嗎?
這個問題很難簡單回答。我是共產黨任命的,所以它能夠影響我。我的大的基調離不開共產黨,我不會走到和共產黨作對的路上去的。我們都是相同體制下生存的人,我們在很多認識上、感情上、價值觀上都是相同的。
我們作為一個市場化媒體,寬鬆度更大,報道的空間更大。我們可以說各種各樣的話,而黨媒、官媒他們不行。這種各種各樣的話可能和官員們他們的感情、想法,有很多是一樣的。
但是是這樣的:我們把這些話說出來了,官員們可能也這麼想的,但是把它變成政策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想法和政策之間有時候有很長的距離,有些想法也許永遠也變不成政策。更何況,我不敢說我的想法和官員的想法都一樣。官員中也有不喜歡我的人,比如已故的吳健民大使,他公開批評了我。
你怎麼知道官員是怎麼想的?
我也是共產黨員,我也在軍隊裏工作過。我有那麼多外交部、安全部門的朋友。我們平時可以在一起吃飯,我們平時有很多交流。我們的感情、價值觀是一樣的,大致的想法是一樣的。但是他們是政策制定者、執行者,他們要更加謹慎。他們不能隨便說,但是我可以說。有些話可能想法和他們一致,但是這不一定會成為國家政策。
外媒有時候解讀我們說是中國官方的報紙,不能說全是錯的,但也不能說全是對的。《紐約時報》代表奧巴馬,代表白宮嗎?代表不了。我們能代表政府嗎?也代表不了。我們和外交部、國防部的關係,也許就像是《紐約時報》和白宮、國務院的關係。
因為都是市場化的媒體?
對,差不多。
那政府從來沒有下令要求《環球時報》寫某篇評論,或者以某個口徑寫一篇評論嗎?
我不能說絕對沒有。但是很少。
什麼例子上有過?
我不想說,很少出現。你知道中國體系裏都會有一些指令,但是對我們和對《人民日報》不一樣。我不能說你說的這些情況是零。但我告訴你這些情況很少。《紐約時報》可能也會有,國務院和他們說寫個什麼東西,可能有關係和他們說,悄悄告訴他們。
《環球時報》可以反映主流的民意嗎?
我不能代表大家,我只能代表我們的編輯部。但是我和主流民意很接近,因為我們在維護國家利益,國家利益是大眾的根本利益,是大家利益的最大公約數。
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有沒有產生衝突的地方?
政策上會有。比如黨說了一個具體的政策,老百姓當時不接受,有些小摩擦,這是會有的。但是我相信,共產黨的根本利益和老百姓是一致的,否則它早死掉了。
如果在具體政策上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衝突,你會反映誰的聲音?
那我看誰對了。如果老百姓的態度很對,我就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。但是批評官方我會婉轉一些,不是死撞。因為明天還得搞關係,我不會狠狠地撞它。但是我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。有時候官方的立場我覺得是對的,民間有一些民粹主義的聲音來反對,這個時候我就會更加站在官方的立場上,勸說老百姓。我不挑撥官民對立,我希望他們能彼此溝通。
你會因為你寫的社評被官方懲罰嗎?
會有的。我們有媒體管理體系,在這個體系當中,我受到批評,會有的。
四月環球網有個民調,問「3-5年內」是否是武力收復臺灣的最佳時機。媒體報道《環球時報》為此被網信辦警告了?
是真的。這種事情經常發生,但這也沒有什麼,我不是還坐在這兒嗎?媒體是一個實踐機構,不是理論機構。我要做一些具體的判斷,這些判斷有時候就可能和某個政策發生一些摩擦,可能就批評我幾句。批評就批評吧,我們做工作改進。但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,不會影響我的工作積極性。這是體制內的某種常態。
你做總編輯11年,你覺得體制是放開了還是收緊了?
波浪式的。總體上是放開了,放的開得多,比我11年前。因為現在有互聯網了,互聯網衝破了很多東西,你跟著水漲船高,要開放得多。
為什麼是波浪式?
因為有時候這段時間放得比較開一點,出了問題就要收一收。過一段時間,又會放開一些。這是因為國家也缺少開放媒體的完整經驗,需要反覆實驗、探索。我認為中國體制總體上還是希望促進輿論開放的,這從大趨勢看得很清楚。
現在處於高波還是低波?
一個波浪的東西,看清它的大形態恐怕最重要,而不是分辨一個時點的位置。
媒體都是西方發明的,在西方產生的。進入中國以後,和中國的政治體制並不全適應,它就要進行中國化。怎麼中國化?中國有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的權利,憲法裏寫著。
怎麼做新聞自由?又要新聞自由,又要堅持黨的領導,怎麼能把它們結合起來?那麼就要嘗試,不斷地嘗試。
實際上國家在努力地嘗試着推動一種中國式的、健康的、社會能夠接受,體制能夠承受的、長時間的、可持續的輿論表達空間,或者言論自由。那麼這就要不斷嘗試:放一放,收一收。一定會是這樣的。
最近提出黨媒姓黨,輿論鬥爭,敢於亮劍,這是想要收緊嗎?
我不認為。它不是要收緊,而是要讓媒體扭轉一些。前一段時間微博時代、微博最火的時候,我覺得媒體搞過了頭。搞過了頭它就要做些調整,它就要強調媒體要姓黨。同時要保持媒體的戰鬥力。
中美意識形態鬥爭

聊一聊美國大選,希拉蕊和特朗普,你支持誰?
我怎麼能支持誰,這是美國的事情。
兩個人對中國都是很大的威脅?希拉蕊的重返亞洲戰略,特朗普在言論上對中國不利。
我把他們大選當做一場熱鬧看。我分辨不出這兩人當選到底哪個更有利。但是我相信一點,中美關係勢比人強。這麼大的利益體系,不是由某一個人決定的。不是特朗普、希拉蕊裏想怎麼扭轉就怎麼扭轉的。
我相信中美關係自然有一定的定力。當然中美關係現在相對比較緊張一些。這是由於結構性矛盾:中國崛起,美國擔心,亞太再平衡,所以有一些矛盾。但這個矛盾有自身的規律,個人的影響相對有限。
你們的一篇社論提到特朗普說明了西方的民主有問題?
當然了。他說了極端的話,能走向這個位置,大家能夠歡迎他,這難道不是問題嗎?美國自己都這麼認為,共和黨都反對他。西方的民主有問題,但是中國的制度也有問題。我們自己也有我們的問題,我們去改革。西方有問題不去改革,它覺得什麼都是對的。
中國需要民主嗎?
當然需要。我們這麼多年一直在推動民主,民主越來越多,包括在基層。我在(總編輯)這個位置,每年環球時報都要投票。如果我非常不受歡迎,那就非常麻煩了。
需要民主,不需要西式的民主?
對,我覺得西式的民主對中國不行。比如一人一票的選舉在中國一定不行,非亂不可。
中國需要協商民主,實質民主,就是老百姓的意見要真正受到重視,官方要為老百姓的利益謀事工作。現在大多數老百姓的意見,過不了多久就會體現在政府的政策上,民主在成為中國人生活裏實實在在的東西。而如果搞美國式的惡性競爭,大家來投票,按照美國式的方式到中國來選舉,我相信中國馬上就亂,這個國家就完蛋了。絕對不能夠。
那篇關於特朗普的社論寫到: 「美國最好小心自身不要成為世界和平的毀滅性力量,而不是去指摘其他國家所謂的民族主義和暴政。」(The US had better watch itself for not being a source of destructive forces against world peace, more than pointing fingers at other countries for their so-called nationalism and tyranny.)這個邏輯好像在《環球時報》很常見,就是說西方有自己的問題,不要多管別人。是這樣嗎?
這不是我的邏輯,我寫文章從來沒有這樣寫過。你帶著一種印象。但是我認為西方不應該過多干預其他國家的事務,我這個觀點是長期的。第二,西方它的制度有問題,這個問題它應該自己改革解決。但「因為西方有自己的問題,所以它不該干預別人」,我沒有放在一起說過。
但最近你評論了中國抓捕維權律師的事,寫到:「美國警察連續在街頭擊斃黑人…美國的人權和司法公正顯然出了嚴重問題。美國這個時候還有心情和精力來擾亂中國的法律秩序,西方自我感覺這樣好,真是讓人驚歎。」
這個沒有問題。不是那個邏輯。我只是感嘆,美國自己的法治沒有搞好,來說我們這兒,我覺得很有意思。如果在中國出現這種事(如達拉斯槍擊),這時美國出一個(人權的)事情,我們不好意思去評論。
所以不是在說你出了問題就不要來說別人了,沒有這個意思嗎?
這個邏輯可能也有一些。但不是我的主邏輯。認為美國有問題,就不應該批評中國——這不是我的主邏輯。
但有時候我會這麼認為:你自己都不怎麼樣,你還批評我幹嘛?這是人之常情。有時候在一個情境下是可以這麼說的,但這不能作為真正的原則。不然這個世界誰都不能批評誰了。
你覺得西方對於中國的批評都是抱著惡意的嗎?
不一定都是惡意,有偏見這是肯定的。利益、價值觀和偏見會使得西方在批評中國的時候失去一些客觀性。他們的批評有時候會夾雜情緒。什麼是惡意還是不惡意,只能一事一議。他們和中國的意識形態形成鬥爭,這種鬥爭都形成一種習慣了,一種條件反射式的。
那《環球時報》對西方的批評有你說的這些問題嗎?
我相信也會有一些。當雙方彼此都形成了一種對立,這種對立存在的時候,我想可能也會有。
有人說你是「愛國主義陰謀論」,你認同嗎?
不認同。中外就和吵架似的,互相吵起來了。他們質疑我們,我們批評他們,雙方難免都有一些過頭話。
總體上,西方對中國的批評,包括人權對中國的施壓,是有建設性作用的。它的建設性作用不是零。從歷史的長河看,西方的壓力對於推動中國人權的進步是起了正面作用的。但這不構成他們批評我們什麼,我們就接受什麼的原因。比如人與人之間很激烈的鬥爭,就相互挑毛病,你就會很小心,你就會做得更好一些。但是具體一事一議的時候,我該怎麼和他鬥爭就怎麼鬥爭。我們絕不能讓西方為中國如何發展人權設置議題、路徑和時間表。那樣的話,人權就會成為西方撬動中國的政治槓桿。
你提出「複雜中國」論,有人認為這是給改革找藉口,任何一個國家不都是複雜的嗎?
我堅持我的觀點,中國就是比其他國家複雜。中國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樣。我們隨時需要驗證這個政治制度的合理性,美國不需要,印度也不需要。因為世界上都是那樣。他們辦錯一件事,錯了就錯了,大家不會往政治制度上去想。
美國和西方都認為很多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引起的,他們的這種看法影響了部分中國人,其實不是這樣。很多都是階段性的問題。但大家都往政治制度上去聯想,好像你一民主一選舉不都解決了,一選舉不都沒腐敗了。一選舉就沒腐敗了嗎?印尼、印度、俄羅斯都是選舉的,多腐敗。
第二,中國正在社會轉型,從計劃經濟向社會經濟,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。但是我們趕上了一個互聯網時代,全球化時代。過去我們有一個錯誤,很多人不知道,慢慢就挺過去,改了就改了。現在中國這麼大的一個社會,基層隨便一個問題就能變成全國性的問題。西方國家都完成了這個轉型,但中國在轉型的過程中趕上了這東西。
曾經的六四抗議者

你參加過89年的六四?那是什麼樣的場景?
你回去看片子。我當時就在廣場上,很激進。
有拍到你?
應該沒有拍到。我當時穿著軍裝,所以比較注意一點。
有參加絕食嗎?
沒有,我不是絕食團的。因為我是軍人。當時即是學生,又是軍人身份。軍人是有軍紀的,非常嚴格,要是他們發現我在那兒就會把我抓走。我上學穿著便裝,但是我自己會比普通的學生要小心一些。
你在清場前就離開了,因為要不然就畢不了業,不能到《人民日報》工作了?
那段時間細節我不想說了。反正我在清場之前走了。
《人民日報》時期你去了南斯拉夫做了三年戰地記者?那段經歷是什麼樣的?
我看到他們打仗,看到一個很好的國家給打碎了。我在那裏遇到一個美國的老記者,他告訴我共產黨是中國的凝聚力量。共產黨應該現代化,但是它的領導力決不能被削弱。一個美國的老記者推心置腹地跟我說。
他是哪個報社的?
我不想說。一個美國非常老的老記者,很有經驗,很著名的一個記者。當時我和他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南斯拉夫過去是共產黨的國家。它解體了變成各個國家的政黨,幾個政黨全鬧獨立,就打起來了。所以(中國)共產黨絕對不能失去對這個國家的領導力,否則中國就亂了,他告訴我。
去之前沒有意識到?
六四沒多久我就去了蘇聯。在那之後,蘇聯解體了,大家很震動。我是學俄語的,蘇聯那麼好的國家,過去是我心中的天堂。後來蘇聯解體了之後,變得這麼窮,在饑荒的邊緣,比中國還差,我看到那個國家給鬧成了這個樣子。我然後又從蘇聯去了南斯拉夫,打成了那個樣子,這對我有很大的震動。
我知道過去有很多東西是我們的理想主義,但可能現實和我們的理想不一樣。兩三年前我在烏克蘭的時候,我和一位總統顧問聊天,我說總結一下烏克蘭的經驗是什麼,他想了一下,跟我說:在一個國家發生變革的過程中,政府一定不能失去對這個變革進程控制力。

有擔心中國失去嗎?
是的。我永遠都會擔心。中國這麼大的國家,也許哪天一下子就失去控制了。失去控制很多人沒有見過是什麼樣的,我知道。我也經過了六四,我是當時是一個熱血青年,我們當時追求的目標是什麼,最後變成了那樣一個結局。
我看到蘇聯、南斯拉夫的變化,然後我們中國的發展,這改變了我的看法。中國是我的祖國,我沒有外國國籍,什麼都沒有,我只有人民幣,我的房子在這兒。中國如果亂了以後我們往哪裏逃?
你說過網民罵你你不在乎,那新聞同行之間呢?
罵我的人裏面有一部分就是新聞同行。新聞同行裏有很多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,他們會批評我,沒關係,這很正常。中國社會在分裂,價值觀在分裂。媒體上的活躍人士,誰都不要想只有讚揚聲,沒有反對聲,越鮮明的人,他一定會有一部分人支持你,一部分人反對你。
絕大多數人支持你還是反對你?
從我的微博上看,反對的人還是挺多的。我的微博已經被一群人盯住了。
《環球時報》的微博做得非常好,支持者非常多,很活躍。
但我相信,支持我的人是多數。否則,《環球時報》不會這麼有市場,我走向全國各地講座,不會那麼受歡迎,在大學裏講,經常過道上都坐上了學生。
你公開說過中國的防火牆長期以後會對國家有負面影響?
我當然這麼認為,現在也這麼認為。
你還鼓勵政府放開言路,對非建設性批評有一定承受力?
我難道沒有在承受嗎?那麼多人罵我,我都承受了,我希望政府也能承受一些。我覺得防火牆有用,中國現在不能沒有防火牆。但是國家不能依賴防火牆。防火牆是一個臨時措施,逐漸逐漸地內部得強大起來。強大起來防火牆就沒用了。
那時候是別人防我們了,倒過來搞個防火牆了將來。
講好中國故事
你覺得在中國封鎖信息的情況下,《環球時報》能給讀者展現一個真實的世界嗎?
對世界感興趣的中國人,能通過互聯網看到外部世界的一切。
就我們來說,會盡量去做,我想做不到100%。第一,是我們沒有那麼高的水平。第二,我們在這種環境下工作,可能無形地會受到這種環境的影響,對信息的選擇未必全面。我認為會有問題。但是我們非常努力地、真誠地把真實的世界告訴大家。
《環球時報》為世界傳遞了什麼樣的中國形象?很多外媒引用是批評你們。
我想應該是一個真實的形象,而不是一個光鮮的、模範的中國。我們要說真話我就說真話,心裏就這麼想的。我們也是中國形象的一個元素。中國社會有我們的理性,也有我們的情緒,甚至虛榮。那就不裝,我們是什麼樣就什麼樣,外界不要誤判我們。
外界願意批評我們就批評,這沒什麼大不了的。我們維護中國國家利益,以我們認為應有的方式。批評我們的人一般都同時批評共產黨,同時批評中國政府。中國都挨了批評,我們難道要把自己摘出來嗎?國家都受到這麼多不白之冤,我個人和《環球時報》受點冤枉算個什麼。
沒有想過給世界傳遞一個更好的中國形象?
我認為更真實的形象就是更好的形象。我沒有能力做秀。我認為要忠於這個國家,為國家服務,為人民服務。現在有地緣政治競爭,有很多矛盾。我們自然要承受這些東西。這哪兒是我能改變的?
再說反對我們的世界是誰?恐怕就是西方國家裏的一些力量吧。很多人都說西方就是國際社會就是世界,那眼光太窄了。世界比西方豐富得多。我做不到取悅美國、日本社會裏的保守精英,還有香港的親美親日的那些人,做不到為了取悅他們而放棄自己的原則。
中美之間有兩個競爭:一個是意識形態競爭,一個是地緣政治競爭。現在意識形態競爭其實是次要的,中國也沒想和美國搞意識形態競爭。美國搞他們的,我們搞我們的,井水不犯河水就完了。
地緣政治競爭是沒有辦法的。現在是美國把地緣政治競爭搞得好像是意識形態競爭,把好多中國人都給騙了。
實際上美國擠壓中國是因為覺得中國發展崛起,威脅到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。如果今天印度發展到這個程度,而中國比較弱,美國會和印度較勁去,可能會聯合中國來對付印度。

南海仲裁是典型的地緣政治,中國的官方立場是「不接受、不認可」。中國媒體很多時候都在不斷重複這種立場,這樣的傳播容易被人接受嗎?
策略上可能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,但是大的態度,中國社會和政府是高度一致的:不能丟了這些島,絕對不能後退。當然有的人說還不如和它(仲裁庭在判決時)鬥一鬥,可能效果好一點。但這是一家之言。
你覺得官方媒體有必要把這種聲音傳播出來嗎?
這是我們現在媒體的一個問題。我也希望這樣的聲音,能夠多傳播一點,我個人認為。但是事實上媒體沒有傳遞出來,傳播得少了點。我覺得這是我們整個社會彈性不夠的一部分。我主張還是讓更多聲音多出來一點。
未來10年中國媒體的版圖會怎麼樣?
有幾個因素。最大的還是技術因素,未來的第一大塑造力。第二大就是政治,我們的管理策略,國家不斷在探討。國家也希望社會整體有彈性,沒有彈性也不好。
技術的發展、全球化,所有這些指標都在告訴人們這個社會需要保持開放性。怎麼保持?這是一個國家需要不斷探索的事情。如果中國能和西方關係好一點,這也會有利於這樣的開放。如果和西方的關係緊張,國內也有人鬧事,這個條件就差一點。
中國在向世界傳遞自己的價值觀,比如中國夢,你覺得這種傳播做得成功嗎?
中國對外講中國故事,我認為還是有很大空間。這件事情不完全是宣傳部門的事,是一個綜合的事。行動有時也是講述自己的有力方式。如果中美關係好一點,傳播的空間大一點。
這兩年中國和美國、日本的關係出現了一些問題,他們這個時候能聽得進去別的話嗎? 但是我們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得很好。
